【記者 李金發投稿】
從《白馬走過天亮》(2013)到《沒有的生活》(2018)的這五年間,甚或更早的以前,在言叔夏升至大學離家以後,與家人拉開距離,從南部小鎮到東部鄉間,再到城市盆地的人事流轉,亦從大學生到研究生,再從研究生轉換爲C城的大學教師,似剪接師般從極細的生活細枝中擷取一節節相似的物件抑或畫面拼湊成一塊有縫補過的痕跡之夢,以敘事者的姿態遊走於文字和行距之間。
敘事者雖然還是老樣子,以最少、清晰又帶些含糊曖昧的味道凝練自己的生活與方式,但還是能聽見活生生的她牽著白駒從《白馬走過天亮》的恍惚走了出來,緩緩地在一條稍稍明朗(且自帶陰翳的氛圍)的路徑繼續散步繼續前進,過著「沒有的生活」。許是敘事者已經數年與家與母親拉開了距離,所以對母親赤裸裸的憎恨亦逐日淡化,反之具某種拉開距離後的張力與其魅力,多了些她和母親之間的互動和幽默:
「別吃那邊的野菜。野外的東西都有毒。」
「還有,別在貓面前換衣服。」
「爲什麼?」
「那還用說,當然是因爲人類無法知道貓到底看到了什麼啊。」
這樣一小段精緻的對話,看似沒什麼的,也可能對一些人來說不知其所以然,但我讀到的幽默,除了和韓麗珠一樣不小心噗笑而出,亦稍微與我生命經驗的影子重疊並產生鏈接。宛若聖地亞哥海邊的大人常對馬洛林說的臺詞:你們小孩子還不懂事。簡潔而有力。迄今仍陪伴我成長,在耳裡邊年復一年滋長厚繭。而我,繼續摀住雙耳假裝不懂事,繼續對老媽子、阿嬤或長輩追問禁忌背後的神祕。不過,歲月縱使能改變他們的臉孔和生活方式,可仍無法動搖他們那一輩的信念和堅持;他們還是老樣子,守口如瓶的,以「禁忌不可以問」築建了一道阻隔我和禁忌之間的距離,成爲不可解的隱喻。
類似這樣的阻隔,敘事者似乎也身同感受。
![]() (言叔夏:《沒有的生活》,臺北:九歌出版社,2018年/照片由李金發攝影)
(言叔夏:《沒有的生活》,臺北:九歌出版社,2018年/照片由李金發攝影)
這時候的敘事者還沒戒掉晝伏夜出的癮,經常受到一日時間的限制,因此經常錯開了郵局辦理掛號的工作時間,也錯過了還書的時間,只好趁夜醒之際將一本本藉來且逾期的書投餵給還書箱吃。對敘事者而言,這樣顛倒的生活是由大量的「沒有」所累積而成的,並促使她漫長的日子裡放置自己成一個空罐子裝更多的「沒有」,就如「什麼東西都裝得進來,卻什麼東西也都沒有裝盛。」
這種因無而有,既有亦無的敘述,與韓麗珠在〈「之間」的風景——讀言叔夏《沒有的生活》〉所提的「之間」相近且頗爲精確。這樣的「之間」和「之間」,宛若齒輪般咬合彼此的契合,嘎啦嘎啦逐日不朽地轉動時間的進程,讓人看見敘事者更多未能在《白馬走過天亮》談及當時的未來和現在的過去。
敘事者像是個未能真正在一座城市落座的流浪者,以「某城」、「C城」陌生的稱呼自己曾去過或現在仍來往的城市,尤其「C城」是敘事者描述的新角色。「C城」在我有限的記性裡,似乎不曾出現於《白馬走過天亮》。這可能代表著在那五年間甚或更早的以前,「C城」逐漸融入她的生活裡,但還未真正產生生命的聯繫。例如〈C城的紅花〉中的敘事者以外來者或者旁觀者的身份觀察C城的老人們,亦對老人們和「秋紅谷」展開「無妄的幻想」,以至聯想起童年裡那被父親虐待卻遭噤聲的表弟,但這一切的一切都與敘事者無關,不管是她自己抑或表弟,兩者(不能說是彼此)都是一種過客的關係。
因無而有,既有亦無。
幾近冷意的文字彷彿長滿千萬隻眼睛在C城的各角落。如是陌生化的敘述,敘事者對父親的描述何嘗不是如此?「父親」的原型從《白馬走過天亮》到《沒有的生活》,一直以來都是處於一種「現身」和「消失」之間的狀態,〈刺點〉中的父親亦然。在〈刺點〉中,敘事者回溯童年時和父親參加了他公司的登山活動。在天黑下來以後,山路越來越難行的緣故,年幼的敘事者「緊抓著在我前方的父親的衣角,叫了一聲:『爸爸!』」而這一個「爸爸」以「從前方伸過來緊緊握住了我」回應了敘事者的不安。至此,不管是誰,至少我爲此因無而有的溫馨畫面莞爾而笑。
可是,由漆黑的山路轉至登山小屋的明亮時,光形同某種隱喻也是轉捩點,父親的臉孔由此憑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張陌生的臉孔;原來一路牽著敘事者的人並非真正的父親,而是一個她不熟悉的陌生人。讀到這兒,不僅讓人倒抽了一口氣,也讓人從正面的狀態跌入負面之谷底。至於敘事者真正的父親,他「早已在隊伍的前方,回到小屋裡休息了」。
這種因無而有,既有亦無的生命經驗其實不只是屬於敘事者寶貴的生命經驗,對我們而言何嘗不是?我們的生活其實也是「沒有的生活」,從沒有的狀態到獲得的狀態,但世上所有的物質或者物理都是有生有滅的,包括人的肉體/命壽抑或存在。物質/物理以外的抽象層面,即我們的精神/生命卻是無生物滅的,一直都在,只不過取決於自己是否能掌握得住這份生命的重量以及精神層裡外的自己。或許敘事者就是透過書寫,將精神的容器溢出且多餘的份量收納於方塊字浩瀚的格子裡一樣,那幾乎能承載人之所限的一切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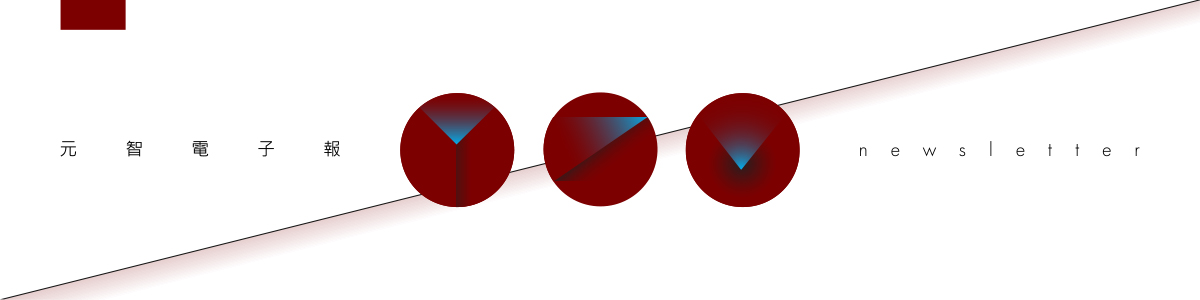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on "因無而有,既有亦無 讀言叔夏《沒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