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金發投稿】
光子是這樣說的:「獨生女的我,守候了母親的死,我無法貼切地說出我得到了什麼。那像是永遠留在我瞳孔中的某種光。當我看著鏡子時,知道我眼中有著以前沒有,如今接收了某種意象的龐大力量。」
《阿根廷婆婆》中的主人公光子在十八歲那一年,臥在病床多年的母親在一個早上告別現世的一切,咬合了光子及其父親往後人生的齒輪,正如我們現實中大部分人一樣,因爲身邊忽然而來的死亡,人生發生了劇動。這份劇動對光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禮物」,也是「某種光」,即便這「禮物」是令人「撕裂胸腔般的痛楚、怕得牙根咬不攏的恐懼,以及一輩子放在心上的醫院昏暗走廊風景」,但「某種光」的積存讓光子逐漸變得敏銳體察身邊的人事物,逐漸變得能夠感受到世間的幸與不幸。
雖言能夠體察到「幸與不幸」,但「不幸」通過吉本芭娜娜拿捏剛好的文字敘述後,總能延伸成「幸」之人事物,最爲關鍵的,即《阿根廷婆婆》往後一大部分圍繞著那滿是奇異傳聞的「阿根廷樓房」,以及那棟樓房的主人「阿根廷婆婆」百合。
除了母親的離世,「阿根廷樓房」與「阿根廷婆婆」起初之所以「不幸」,原因在於樓房與百合的傳聞夾雜的負面內容,以及光子的父親在妻子離世不久便頻密與百合來往,使光子在友人抑或衆人面前陷入尷尬的情態。負念堆疊負念。只要談起父親與百合的事,縱使光子的內心交錯著許許多多外人無法體會的複雜情緒,從而「浮現自己頻繁前往療養院和醫院探病的寂寞身影」此具咀咒性質的想法,她僅能顏面淡定應對,就像聊家常便飯那樣把此事當作一種消遣。直到年月日向往後橫跨一大步以後,光子審視回自己的過去時,非常訝異年輕時候的自己竟正活生生抹殺著父親的存在,如同我們現實中某角落正發生的倫理悲劇——「雖然人在死的瞬間以前明明還活著,卻因爲週遭早早施加的那種小小詛咒,被當成已經死了。」
不過,傳聞終究起源於人們因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而生的臆測(雖然部分內容屬事實)。在父親辭掉石匠的工作並搬至阿根廷樓房後,光子某日決定走訪樓房一趟,而「不幸」就此轉寫爲「幸」。
自母親離世以降,光子一直處於哀傷之中,不過在她鼓起勇氣走訪阿根廷樓房一趟並敲響起門時,百合從傳聞裡走出,以「高尚單純」的姿態現身並開始活躍於光子生命的河流裡。不僅對光子而言,更對光子的父親而言,百合走入他們的生命即點亮了他們逐漸黯然的生活。縱使起初對百合有所警惕,光子逐日與百合相處下,逐日滋長對百合愈發喜歡,不管是最初見面的擁抱而重新滋潤近乎乾涸的淚泉,抑或往後不斷來往及相處的日子,日子堆疊日子,阿根廷樓房與其週遭環境的寧靜、時空裡外的停滯及「沒有一樣東西『不見了』」的特質,與噪世——滿是忙碌的現代生活隔絕,形如類似加斯東 • 巴什拉所提:「一個新的空間向度即將開啟一個私密感的向度」,給予光子一個短暫的去留之處,從而發揮了生物與生俱來並遺傳至今的藏躲特性,「在思緒移轉到其他事物以前,盡情地擁抱悲痛」,藉此進一步獲得安置母親與哀傷的「某種意象的龐大力量」、「某種光」。
然而,這充滿過去、充滿思想的停滯時空僅建立於光子身處的現實之上的感情世界,現實世界的運作依然,時間仍守職地流動著,這也就意味著人之生命力正隨之消逝。所幸的是,這時候的光子已經變得足夠強韌,尤其在接納生與死方面,她透過映入眼裡的一切經驗,透過吉本芭娜娜以「光」輝的色彩爲譬喻,發現百合年近花甲生育弟弟以後,百合和父親的生命力「逐漸溶入那個老舊陰暗的屋中,溶入那素雅的背景色調中」,「只有嬰兒像染上顏色般鮮明浮現」,形同一種生與死的「圈」,說明了生與死不斷以新的姿態、新的姿體降世與離世,因爲這就是生命最自然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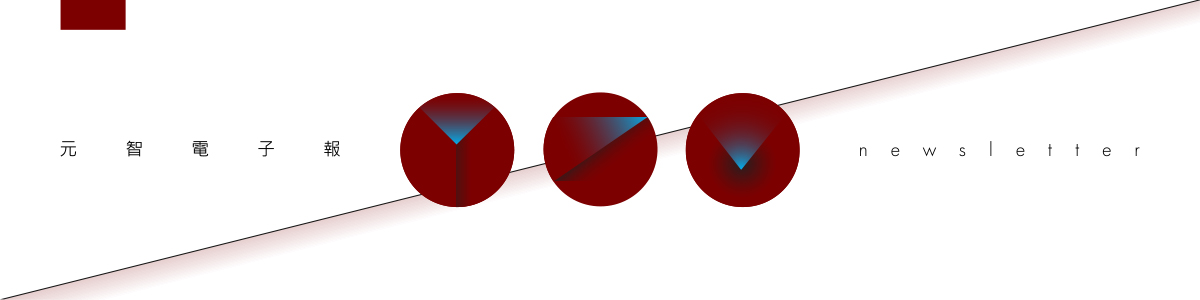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on "接納生與死的某種光 讀吉本芭娜娜《阿根廷婆婆》"